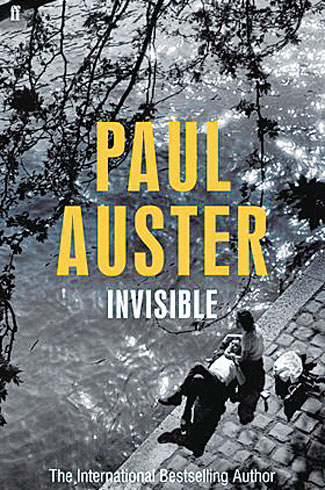
保罗·奥斯特的《无形》(文/蔡宸亦)
集小说家、诗人、剧作家、译者、电影导演等多重身份于一身,被视为美国当代最勇于创新的小说家之一的保罗·奥斯特又出新书了。《无形》(Invisible)上月在英美出版,《泰晤士时报文学副刊》的书评写道: 那些没有读过保罗·奥斯特前14 本小说的读者,大概很难就《无形》想象出奥斯特是如何功成名就的。《纽约客》则视奥斯特为当代作家中最不擅挖苦讽刺的一个。
Roger Phaedo 已经10 年没有开口说过话了,是的,对任何人都没有。他把自己困在布鲁克林的公寓里,近乎痴迷地每天反复翻译卢梭的《忏悔录》(Confessions)。10 年前, 一个名叫Charlie Dark 的恶棍痛打了Phaedo 夫妇一顿,当时Phaedo 生命垂危,妻子Mary 则在紧急监控室支撑了5 天后咽了气。从那天起,Phaedo 白天翻译《忏悔录》,晚上写Charlie Dark—一个从不认罪的人的故事。Phaedo 喝起威士忌从来不当一回事,他借酒消愁、麻痹感官、忘记自己的存在。他从来不接电话。有时,住在走廊另一端的性感女人Holly Steiner 会悄无声息地走进他的卧室,把他从昏昏沉沉中挽救出来,其它时候,眼神尖锐、自私而无趣的职业妓女、Aleesha 会取代Holly 的工作,她就像Holly 的分身,将Phaedo 从黑暗中拉上岸来。
一天,Aleesha 赤裸着在屋中徘徊,无意间瞥到两沓包裹得整整齐齐的手稿,一捆是卢梭的翻译,每页上几乎覆盖着相同的字迹,另一捆则是有关Charlie Dark 的小说,她扫视着纸稿,突然惊叫:“我认识Charlie Dark,他是一个强硬的人,那个混蛋为保罗·奥斯特工作。哦,我真想读读这本书,可惜我通常懒得读厚书,你能念给我听吗?”长达10 年的沉默就此打破,因为,Phaedo 想要取悦Aleesha。他坐下来,开始朗读小说的开场白,也就是这个您正在阅读的故事。
这是文学评论家詹姆斯·伍德(James Wood)模仿奥斯特写的一段“奥式情节”。在《纽约客》上,伍德想证明,奥斯特每回写小说都换汤不换药,你不愿承认也罢,但事实确实如此。“奥斯特元素”包括:主人公总是男性、不是作家就是一个隐居的怪人,不是被老婆抛弃或离异,就是孩子早逝、兄弟失散。接着,作为偶然性象征的暴力事件穿插在情节中,当然也因此引人入胜—一个被抓进集中营里的女人、一个在伊拉克被斩首的男人、一个被正要同她发生的男人狠狠殴打的女人、一个被关在小黑屋并受到虐打长达9年的小男孩、一个意外地被射瞎双眼的女人,等等。奥斯特的对白街头感十足,在一个正邪不分的B 级片氛围中,叙述者让故事充满了现实感。文本中,夏多布里昂、霍桑、 卢梭、爱伦·坡、贝克特的文字总会间隙优雅地钻入。其它必备元素还有:双重性、他我、分身(doppelgangers)以及一个名叫保罗·奥斯特的角色。这些暗示,散乱得就像老鼠稀稀落落掉了一地的零食,最终把我们引入一个后现代的啮齿科洞穴。真相在故事结尾展露:一切我们所读到的,不过是主人公的个人想象。嗨!有关Charlie Dark 的一切,都只存在于Roger Phaedo 的脑海中。
一个诗人的陈词滥调
伍德说,《无形》虽不乏魅力和动感,但终究没有逃出“奥式情节”的桎梏。1967 年,一位在哥伦比亚学习文学的诗人Adam Walker,年仅20 岁,照书里的说法,“要先看看这个奇怪的世界怎样演进”,沉溺在兄弟10 年前坠入湖中溺亡的悲哀中。在一场派对上,Adam 偶遇了一名阴险浮夸,既有法国血统又有德国血统的瑞士人RudolfBorn。Born 是一名座客教授,36 岁,对自己开授的课程法国殖民战争史拥有独到见解,“战争,是对人性对最纯粹最生动的表达”。Rudolf 执意贡献自己的女友与Adam 上床,后来,我们发现Rudolf 不仅秘密为法国政府工作,还很有可能是个双重间谍。Born 迅速对Adam 示好,愿意出钱让Adam 办文学杂志,“我看到了你身上的出众之处,也许是出于令人费解的理由,但我愿意为此博一把”。“出于令人费解的理由”,就像奥斯特急不可耐地在招供自己灵感缺失。
又一个典型的奥斯特故事,偶然性就像天上掉下来的摩托车。一天晚上,Adam 与Rudolf 在河边散步,一名持枪的黑人拦截了后者,Rudolf 拔出自己的弹簧刀,无情地刺杀了这个连枪都未上膛的可怜的年轻人。第二天,Adam 收到了Rudolf 的威胁信,要他闭嘴。令人感到耻辱的是,这名本该心存梦想的诗人却报了警,最后Rudolf 不得不潜逃到巴黎。
Clichés,老套、迂腐、陈词滥调,是现代或后现代文学里的常客。在福楼拜眼里,陈词滥调就是被玩弄、紧接着被杀害的走兽。《包法利夫人》里代表迂腐的查尔斯·包法利的话,被比作一条许多人都走过的路(a pavement overwhich many people have walked); 在20 世纪的文学里,陈词滥调就像一条借来的纸巾,沾满了众人的鼻涕。现代和后现代作家诸如贝克特、纳博柯夫、理查德· 耶茨(Richard Yates)、托马斯·伯纳德(Thomas Bernard)、 穆丽尔·斯帕克(Muriel Spark)、马丁·艾米斯(Martin Amis)以及大卫·福斯特·华莱士(David Foster Wallace) 都在作品里调侃并戳穿过陈词滥调。
不知不觉的现实主义?
奥斯特,作为美国最好的后现代作家(如果以数以千计的前卫小说外行都读过《纽约三部曲》为证据的话),在涉足借用“Clichés”时,却并未对此锦上添花,这是多么扑朔迷离啊!表面上,奥斯特是个奇特的后现代主义者(又或者,他完全反对后现代?),可是,他80% 的小说又几乎与传统的美国现实主义一鼻孔出气,剩下的20%,往往因加入了对情节真实性的怀疑,如同脱胎换骨了80% 的后现代手术。
奥斯特的小说读起来非常快,如梦呓一般,语言上与许多现代主义作品非常相似,没有语义上的障碍、艰涩的词汇或者句法上的挑战,又因充斥着鬼鬼祟祟的转折、意外、暴力突变,被《时代》杂志评价为“与一般的畅销悬念惊悚小说大同小异”。奥斯特之所以不是一名现实主义作家,完全是因为他的叙事游戏反现实或超现实。在《偶然之音》(The Music of Chance,1990)中,Nash忽然有了一大笔钱,于是他买了一辆新车,开始在美国各地的公路上漫无目的地驾车流浪,直到有一天,当身上的钱快用光的时候,遇到了一个靠扑克牌赌博赚钱的Pozzi。Nash 愿意跟随他进行一次赌博冒险……而在《幻影书》(TheBook of Illusions)中,一位在空难中失去家人的大学教授想揭开一位喜剧演员失踪的谜底,他追查故事的原曲,曲折反复,而读者最后竟得知,一切我们读到的,不过是教授因过度沉浸于悲伤中产生的幻觉。
这些故事的问题并不在于其后现代的笔法、而是奥斯特指望在现实中抽出的,对于情感逻辑的把握。作者自以为最为庄严的时刻,恰恰是最虚弱而乏力的。没有人会相信纳什空洞的坚定以及大卫醉生梦死的悲伤。他们的情感动机就像好莱坞电影里一推就倒的故事大纲,而奥斯特则滑稽地指望读者同他自己一样对此深信不疑。
奥斯特要追求常规现实主义的情感可信性,也要一种后现代词语游戏的战栗感,结果却得到了虚假的现实主义和一种浮浅的怀疑论。奥斯特的故事很强势,却是用断论代替了说服。这就是奥斯特无法匹敌萨拉马戈与菲利普·罗斯(Philip Roth,著有《鬼作家》)的原因。萨拉马戈的现实主义中夹杂着怀疑主义,然而,他的怀疑主义令人感到真实;罗斯的叙事来自于他对人类喜剧与讽刺的观察,萨拉马戈与罗斯,并未试着像寓言那样模拟人类,可他们解构和反解构的结果却殊途同归。相比之下,奥斯特尽管耍尽花招,却可能是当代作家中最不擅挖苦讽刺的一个。
《泰晤士时报文学副刊》将《无形》的受众界定为,要么是搞文学创作的知识分子,要么是对猜谜或莫比乌斯结构痴狂的人,要么对拉康的理论感兴趣,要么是一个亲法论的怀疑者,要么则是个后现代主义者的高度接受者。要是不满足于以上任何条件,你就得怀着十二万分的耐性,去容纳一个由无形的作者构筑的充满未知谜底的世界,同时,小说的回报极其微妙。
宾夕法尼亚大学英语文学系教授BillBroun 写道:毫无疑问,奥斯特是刻意要让《无形》的读者极其小众,而他的无病呻吟、时不时的过度诠释、散文化的笔调、平庸的艺术气质、中产阶级的人物也确实起到了“推波助澜”的效果。要说人们之所以无法忍受结尾,那是因为,根本就没有结尾。除了对主题的演化作用的考虑外,作者对人物分身的分化与发展实在兴趣贫乏。








